“智能制造 反思與期望”——沈烈初在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
“智能制造 反思與期望”
——沈烈初在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
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筆者今年正86歲耋耄之年。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學習、工作及生活在這70年的全過程,有幸參與、目睹了世界與中國百年大變革的大部分時序。我經常定位于一個退休的老者與回歸到一個草根知識分子,與各方沒有利益牽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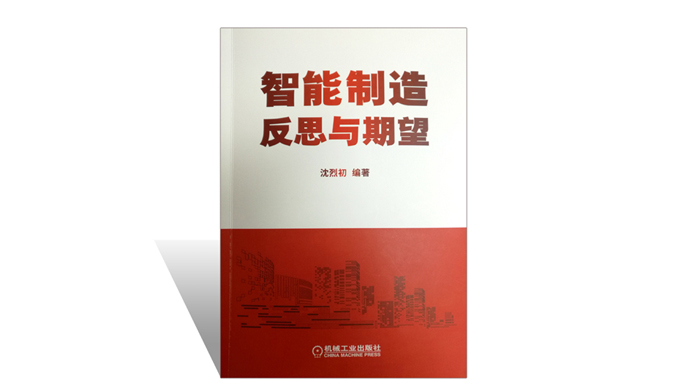
一、反思
在這一段時間中,有幸學習與觀察世界G7(或G8)及其他部分發達國家各行各業制造業至少600-700個企業。同時有幸觀察了這些國家高等院校、研究院所,有關管理裝備工業的政府、協會、學會等部門,經歷了工業2.0到工業3.0工業化全過程,發達國家已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在國內我也經歷和觀察了工業1.0、工業2.0及有條件的大中型、外向型企業全面建設工業3.0的數字化、網絡化制造或兩化融合,工業4.0還是一種設想或試水。這一段時間中我也親身參加了產、學、研、政領域的工作,有機會觀察學習了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不同地區的企業至少達二三千家。同時,有機會與很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學會及協會的領導、學者、專家進行研討。這些經歷使我對工業1.0、工業2.0、工業3.0的時代特征有了深刻認識,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實屬不易。到目前為止,中國制造業仍處在不充分、不平衡的發展階段,工業1.0、工業2.0、工業3.0時代的企業都存在著,大量企業還處在工業1.0、工業2.0時代,加上區域發展更加不平衡,全面實現工業化的難度就更大了,需要國人加倍努力。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互聯網、物聯網、傳感網、工業互聯網、互聯網+與+互聯網、數字化與數字經濟、大數據與云平臺、機器人、人工智能、智能+,通訊技術也由2G到3G、4G,目前正在由4G向5G過渡。宇航、新材料、新能源等新技術爆發性的發展,人們都跟不上,眼花繚亂、不知所措。智能制造上升為國家戰略之一,已經實施6、7年了,需要進行不斷的反思與總結,使其發展更符合中國國情,更加健康地快速發展。
我先把幾個時代的特征簡述如下:
工業1.0:機械化(蒸汽機發明),十八世紀;
工業2.0:電氣化、半自動化(硬件控制),電力、電機裝備的出現,十九世紀;
工業3.0:數字化、網絡化,即信息化,可以出現全自動化或者無人化(少人化)企業與車間;電子計算機、大規模集成電路、PLC等發明,有可能用硬件與軟件進行控制,集中在二十世紀后半期爆發式增長,引起新技術革命。
工業4.0:即信息化+人工智能=智能化。
制造業智能化的三個領域
裝備產品的智能化控制,即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三化控制);
裝備生產過程的智能化管理(三化管理);
用戶服務的智能化(售前售后、定制化及用戶使用產品時的在線檢測,提高用戶使用水平,產品的健康檢查,實施升級提高或再制造等),即產品全生命周期(PLM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
二、經歷
改革開放40年中我就關注研究機械工業(裝備工業)如何迎接新技術革命,比較系統闡明我的思想的有3篇文章:
1、1985年發表的“新技術革命與機械工業發展戰略”提出:機(械)電(子)儀(傳感器)一體化概念,并提出3個結合:工藝與裝備結合、軟件與硬件結合、技術與管理結合。
2、2015年五一勞動節發表“讀《中國制造業2025》與德國工業4.0后的思考”,特別分析了中德兩國官員、學者、企業家等之間不同的理解,包括:戰略目標、制造業的基礎、兩化融合水平、領導與員工等人員的素質、制定的方法,德國是自下而上,中國是自上而下。
同時,提出幾個可商榷的問題:(1)CPS系統的理解;(2)人工智能概念;(3)兩國工業進程的差異;(4)互聯網+與+互聯網的理解不同;(5)傳感器與數字采集,即數字化的實踐等。
3、2016年6月,撰寫了“裝備工業實現智能制造認識上的疑問與思考”,包含以下內容:(1)裝備控制的“三化”(即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下同)和產品生產過程的“三化管理”應齊頭并進等有關問題;(2)實現智能制造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要靠企業自己的內生動力推進;(3)應正確對待實體制造業與虛擬制造(即數字雙胞胎或孿生數字技術,仿真技術或CAE);(4)德國信息化架構RAMI4.0與中國版4.0架構的比較;(5)不同工業化階段,決定了智能制造的切入點不同,需要頂層設計、分階段實施(即一廠一策);(6)標準化和規模化是智能制造實現的基礎,并提到我國企業在產品設計與生產過程中精益生產與準時化管理方面差距更大;(7)對于如何看待“智能制造工業園”,筆者認為沒有必要,會造成社會資源極大的浪費;(8)軟件、傳感器與系統集成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9)關于智能制造深層次的工作:標準、安全、培訓、監管、資源、效率等。
三、探討
中國工程院在2017年提出“中國智能制造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征求意見稿)”,并提出“新一代智能制造”概念,我進行了仔細研讀,收獲很大,但仍有一些疑慮,因而我在2017年12月提出了“關于智能制造發展戰略的八點建議”。
在以后不到兩年中,結合我在過去四五年中考察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不同地區二三十個兩化融合案例并剖析,加上過去幾十年對國內外數千個企業的記錄與記憶,一共撰寫6篇“論新一代智能制造發展戰略”的文章,期望得到行業內專家的指正與切磋。技術發展要因地、因時、因發展不同的階段而實行不同的發展戰略,不要一刀切,以這種運動式的方式發展新技術,可能帶來很不理想的結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智能制造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創新驅動,從產業鏈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推進,提質增效,實現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做專、做精、做強,每個企業有著自己的殺手锏立足于行業之林、世界之林,不是所有企業要做大,也不可能都做大,要形成制造業結構的“金字塔”,由大多數中小企業隱形冠軍組成堅實的基塔,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這幾十年來,我采用實踐論、矛盾論、系統論與控制論“四論”來觀察世界、分析企業的發展,并將其作為我觀察事物及企業發展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加上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來研判與剖析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高新技術的研發與應用,使其與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筑的改革調整辯證地統一起來。新的生產力要求企業的上層建筑,包括企業文化、思維方式、管理模式、產權關系等都要優化,使其適應新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能加速推進新技術的應用。特別是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每一個企業的產品作為全球產業鏈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新時代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將加速企業的優勝劣汰。
去年下半年,由原機械部陸燕蓀老部長提議,由機械工業儀器儀表綜合技術經濟研究所石鎮山副所長等幾位博士、專家認真編輯、修改,由機械工業出版社精心策劃出版本書《智能制造 反思與期望》,并榮幸請到工業和信息化部苗圩部長寫序,我實在擔當不起,在此我對這些領導表示深深的敬意與謝意。這是我正式出版第一本專業論述,我將倍加珍惜。
出書的目的是請有關的領導、專家、企業家、技術與管理人員指正并切磋,引起大家的討論,我將虛心聽取行業內讀者的指教與批評,共同推動作為實體經濟基礎的制造業的發展,在習近平新時代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機械工業高質量發展,做一塊小小的鋪路石,以此表達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責任與擔當。
沈烈初
2019年10月



